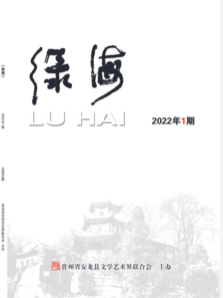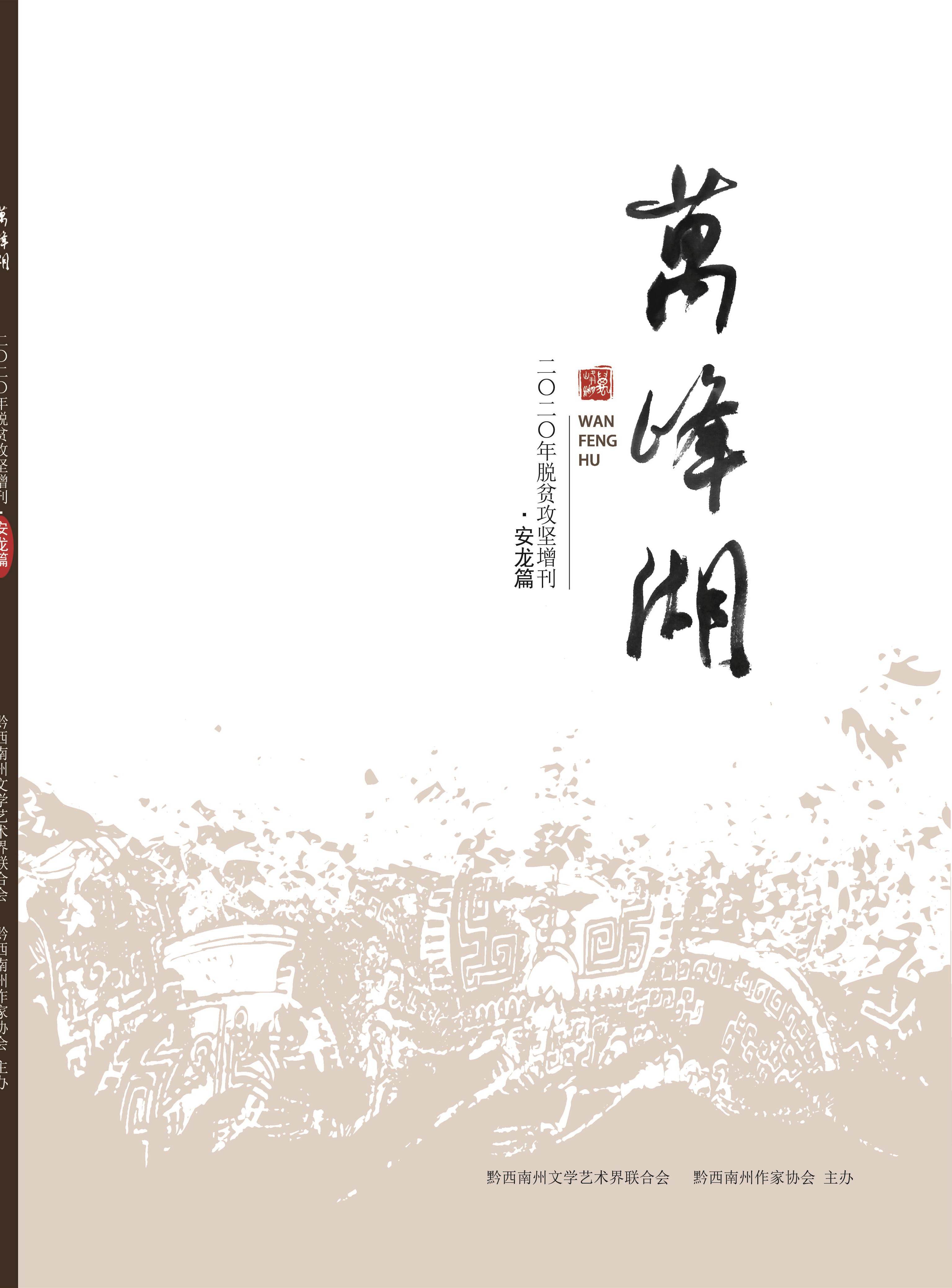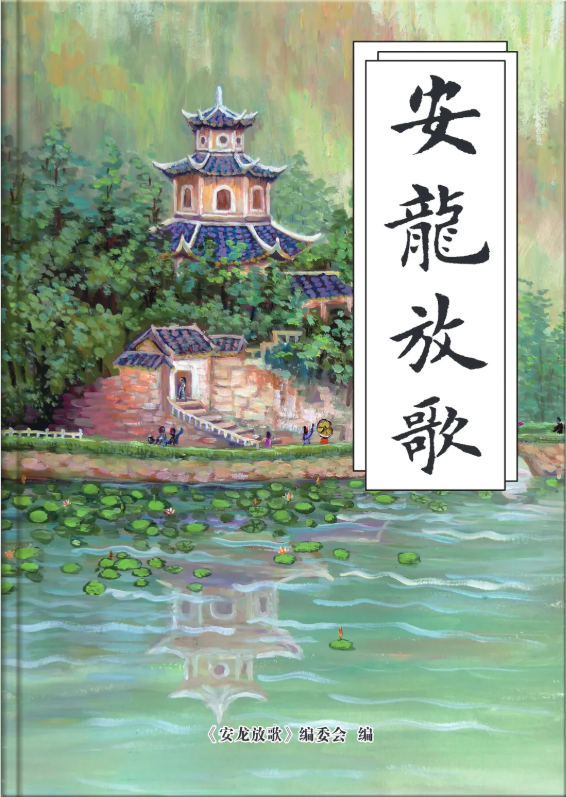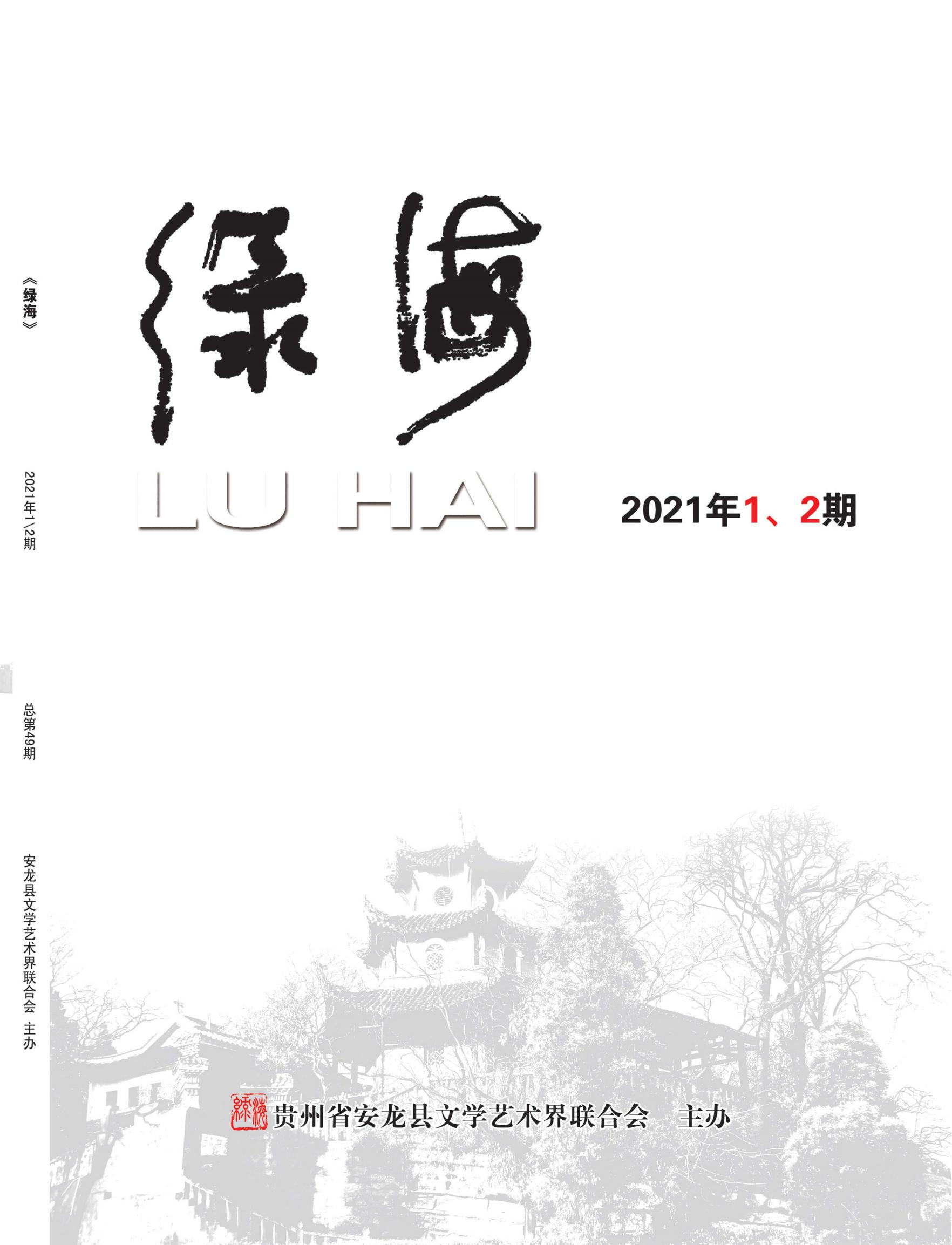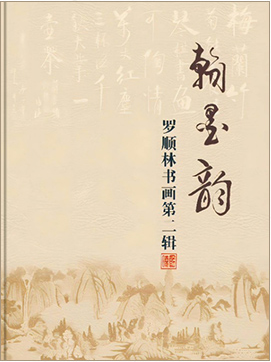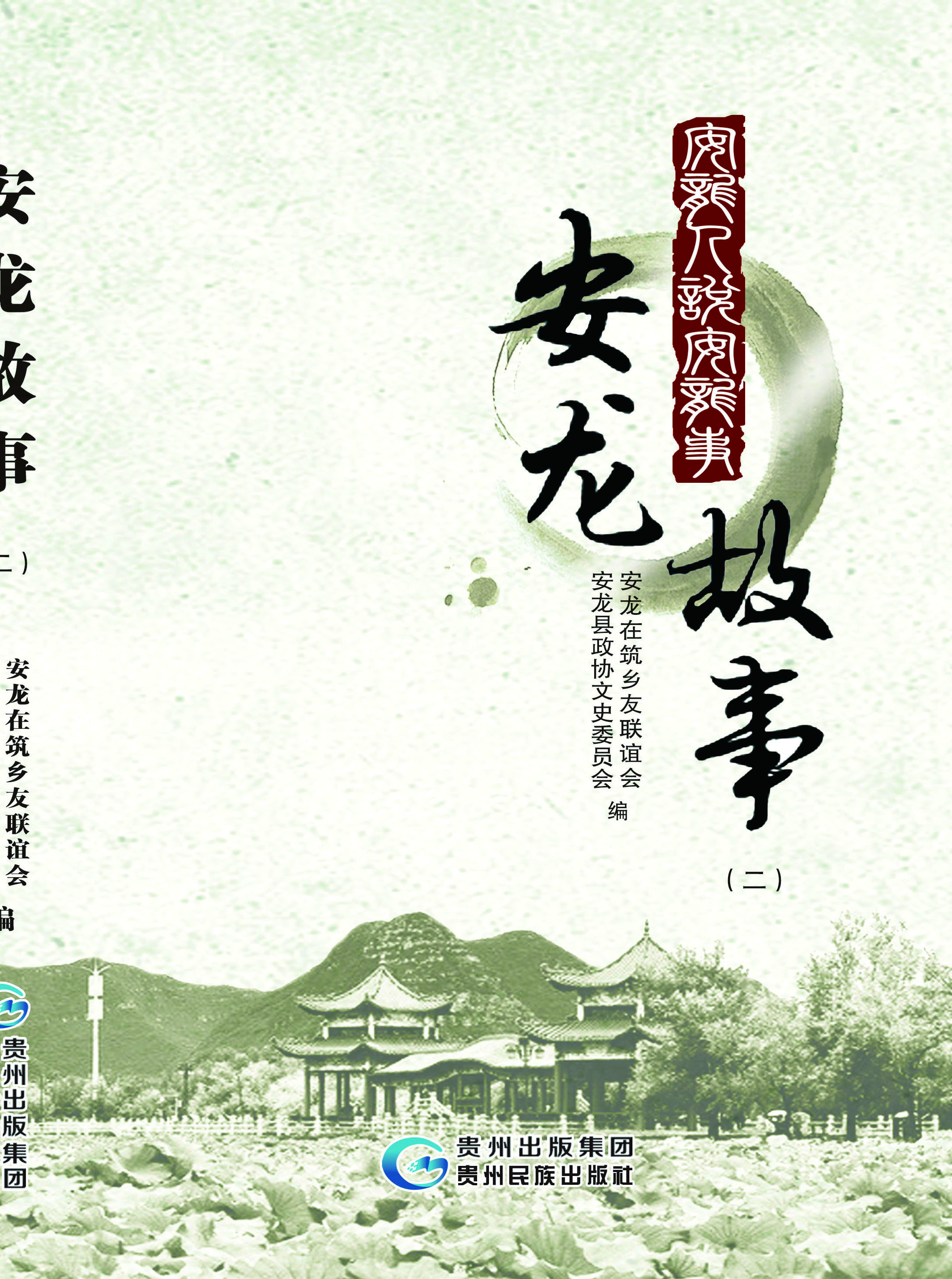我出生在离荷城不远的布依村寨,年少时,经常跑到荷池里玩要,也算是生活在一个以古莲子而闻名的小城。
盛夏,满塘莲花,风吹荷动,清香萦绕。莲花的香,与别的花儿不同,淡雅清丽,若有似无。当然,我也喜欢莲花的风骨,出淤泥而不染。远远望去,波光潋滟,一塘碧萍染了半边天,连塘边的垂柳也被染得多了几分醉意。
当时全县就一所中学,初中招生考试竞争激烈,四五千个小学毕业生应考,而安龙中学初一新生只招200名。我就读的平乐民族小学,以前几届毕业生要么考取一个两个,要么就是“白板”。我们那一届,40个同学一下子考取了7个,创历史新高,轰动全县。毕业会上校长激动得流出热泪,我们的班主任韦洪思老师因此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在荷城学习生活整整六个年头,算得上老资格的荷城人。那时候可真年轻呀,年轻到像一张白纸,连“喜欢”这两个字,都是如此的纯粹,没有丝毫杂质。
我曾和一群写诗的朋友一起,从学校步行到荷塘读诗、写诗。我不会写诗,至今都不会,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当一个听众。那是一个为诗倾倒和狂热的时代,我们读顾城,读北岛,也读舒婷。
我们喝从老家带来的布依“便当酒”,读诗赏莲,乐在其中。读别人的诗,写自己的诗。当然,那些诗写得不怎么样,严格说来是纯粹的“打油诗”,却表达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是青春的挥洒,是快乐的源泉。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却并不影响我为之狂热和倾倒,因为那些诗句像火把一样点亮了我们的青春,照亮了我们今后的人生。
我们去看小人书(连环画),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荷城很小,东起招堤公社,西至大坪公社,距离三五华里,骑着单车,半个小时就能把小城绕一圈。县城唯一一家电影院坐落在繁华地段顺城街北门洞十字路口左侧。每天日落时分,当夕阳把电影院印成剪影时,我们便骑上单车,跑去看看墙上的海报是否换了新的,是不是又上演新片了,那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电影院大门两侧,摆着书摊,清一色的小人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名著,也有《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那个时代人津津乐道的读物。一本一分钱,包你看个够,是等待电影开演打发时光的好去处。
售票的女孩是电影院门口的一个“招牌”,两条长长的麻花辫,红嘟嘟的嘴唇,齐齐的刘海儿。有留长发、穿喇叭裤的男孩隔老远对她吹口哨,她不屑一顾的样子,很俏。
如果现在要问我对电影的印象,只怕那售票女孩比电影院银幕上的形象更让我记忆深刻,因为她红嘟嘟的嘴唇,是那个年代中的一抹亮色。
可惜后来电影院改成了录像厅,门口两侧的书摊也改成露天“卡拉 OK ”,录俊厅里面进进出出的多半是浓妆艳抹的女人和痞里痞气的男人,满屋子乌烟瘴气和一地的瓜子皮。
电影院没了,没有去处,青春的脚步仿佛一下子停滞不前,我们变得像一只只被圈起来的困兽,乏味地骑着单车在小城里东游西逛,对未来没有幻想,对青春没有奢望。
后来,我们常去小城西边的汽车站,因为我们向往远方,我们想坐汽车去小城以外的地方,看看天有多大,看看地有多远。
起因是邻居家一个姐姐跟着恋人私奔,就是从这个汽车站出发的。这件事让我深受刺激,我忽然对那条宽阔的公路产生了好奇,觉得它很神奇,因为它一直通向远方,可以让人去想去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新的去处,那就是小城那小而破败的汽车站,看着那些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人发呆,任时光在墙上慢慢地游移,设想着有一天,我也会像这些人样,捏着一张属于自己的汽车票,沿着那宽阔的公路,去远方。
恢复高考那一年,我和那群在荷池边赏莲写诗的同伴考上省城高等院校。我们结伴从小城小而破败的汽车站出发,跨过北盘江,来到比小城大数倍的省城,我们或在师院,或在医学院,或在工学院,或在农学院求学,圆了各自的大学梦。
我们学成归来,在小城各行各业工作,为小城的建设出力……
时光像一只手,抚过的地方就再也回不去。
岁月流逝,我们的青春遗留在了小城。我的小城时光,我的仓库一样腐朽的电影阮,我的破败而陈旧的汽车站.我乏味而狂热的青春……
有人问我,如果可以选择还愿意重过一次那样的时光吗?我点点头,又点点头,我真的愿意,那旧照片一样散淡泛黄的时光,因为纯粹而美丽,因为美丽而盛开,漫过匆忙的岁月,凸现在人生的底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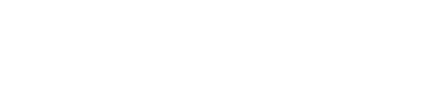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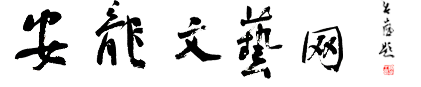



 热门阅读
热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