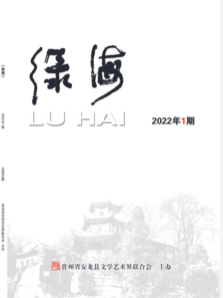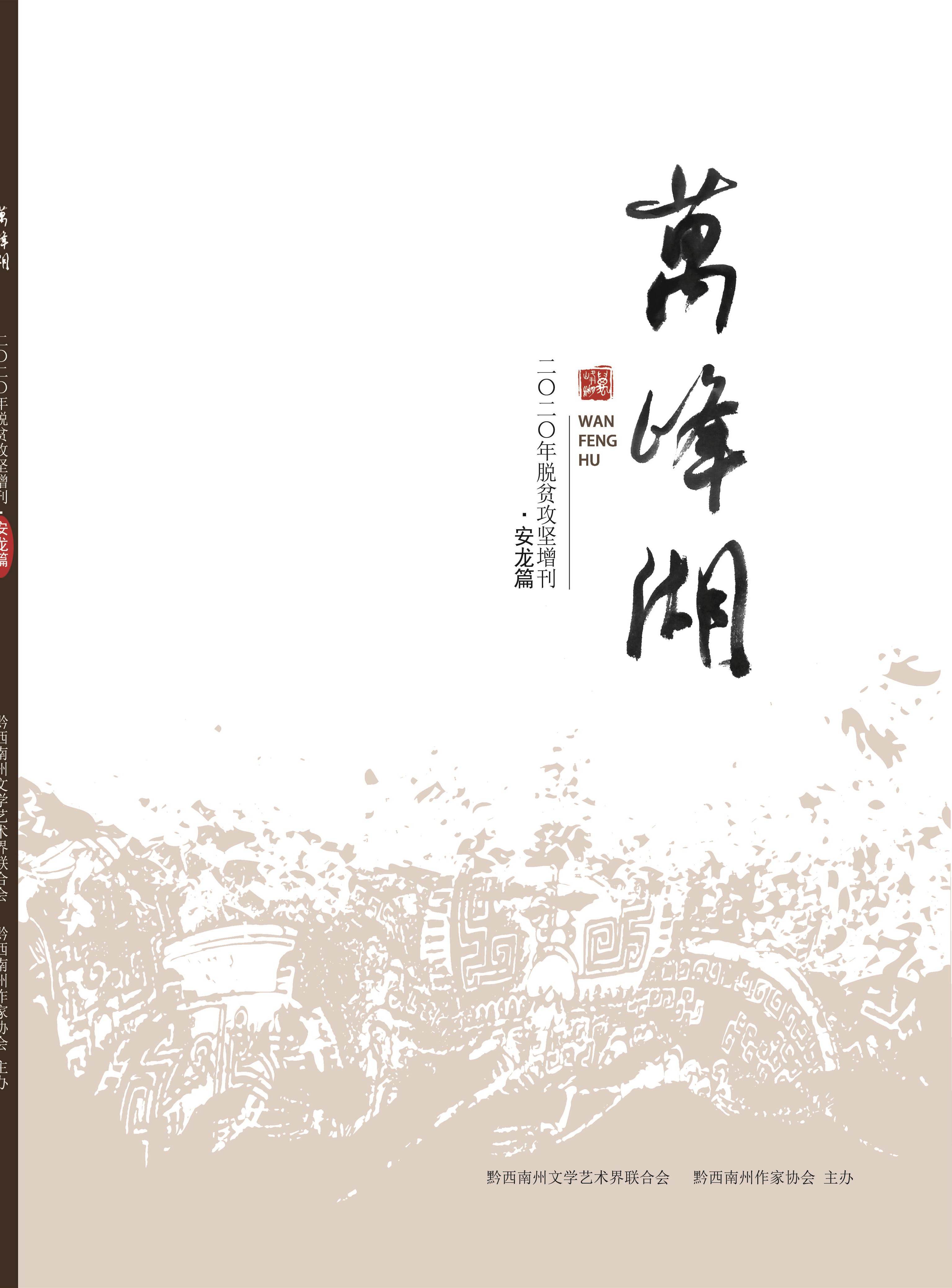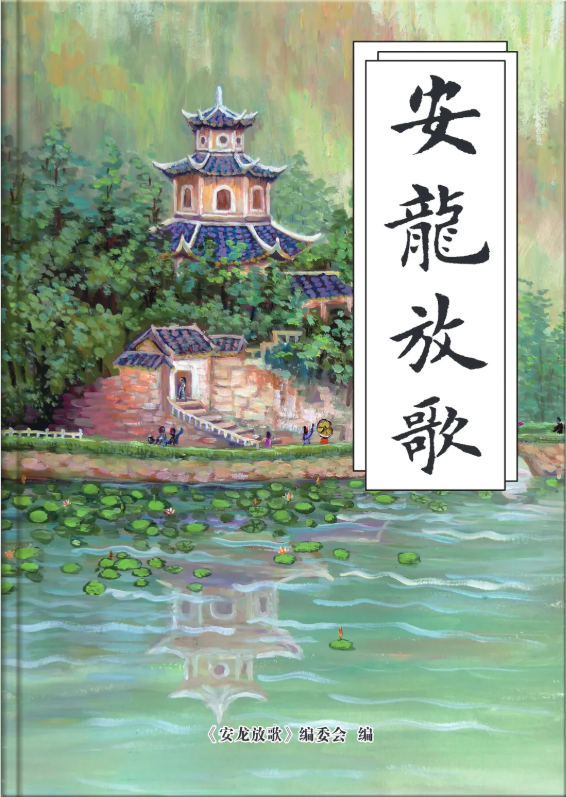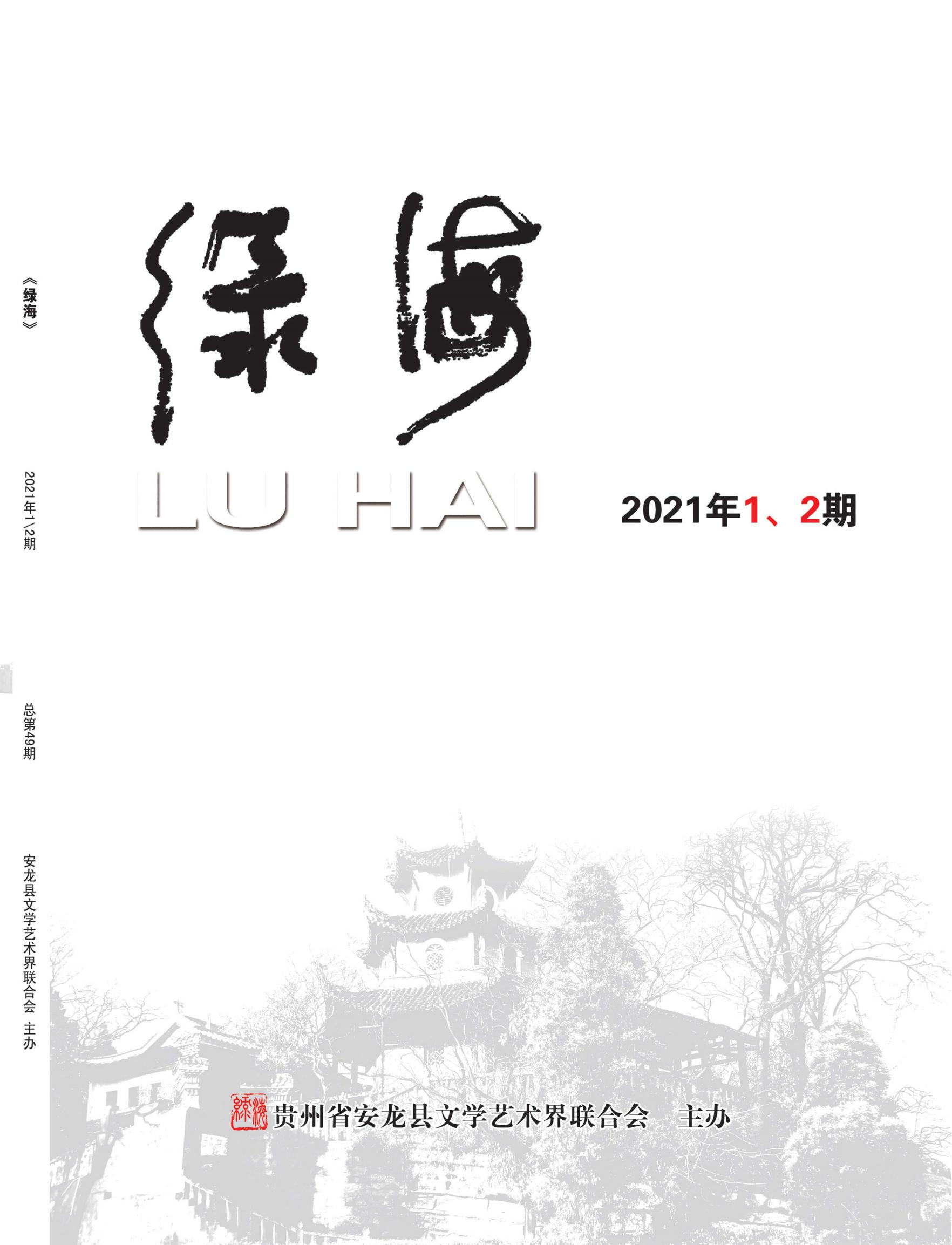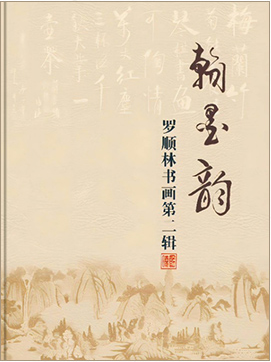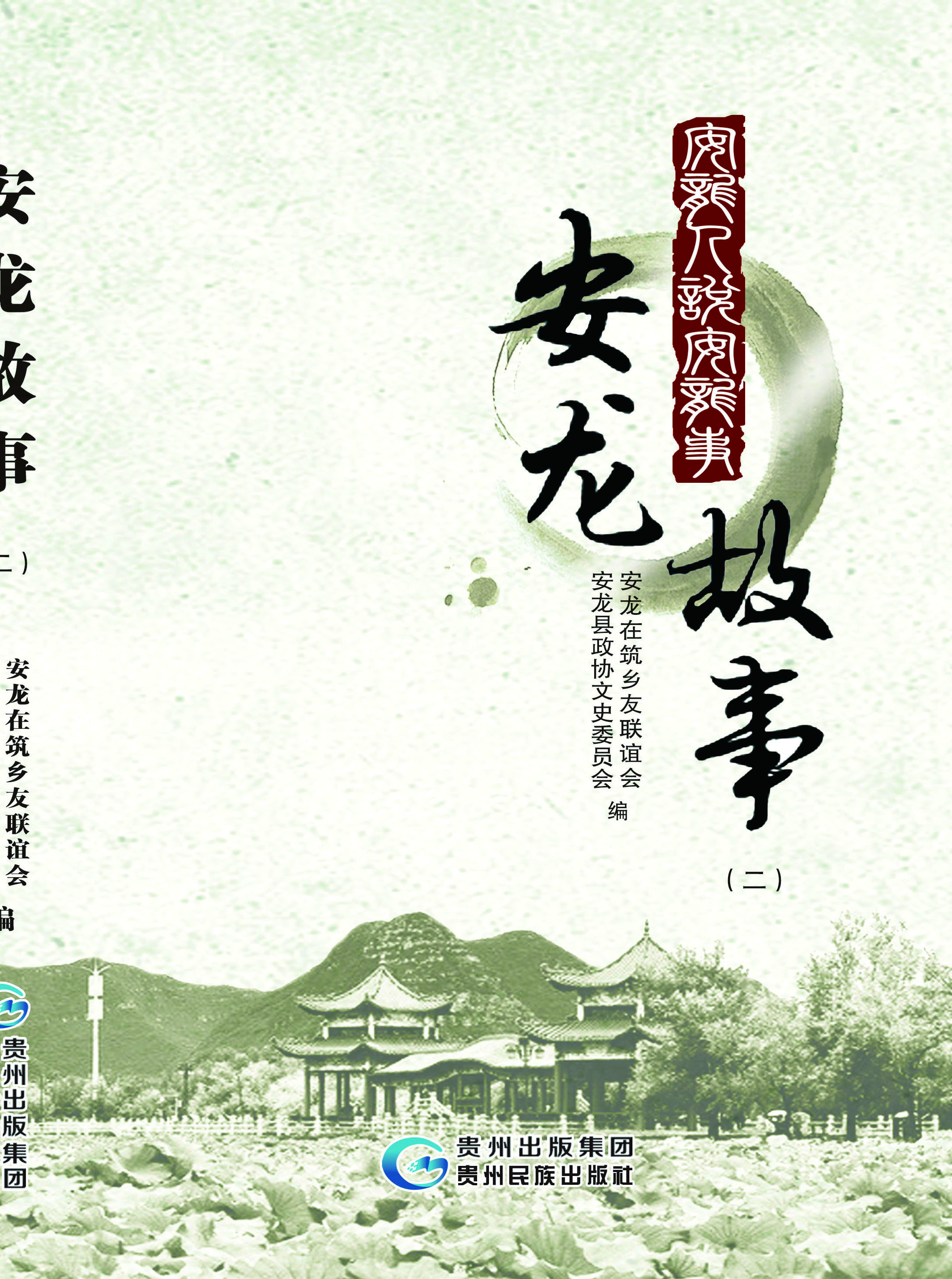到了安龙县龙山镇究竟看什么、听什么、品什么?是看山、看水?还是听历史、听传说?抑或品人物?在笔者看来,这一切都值得看,值得听,值得品。看山,看的是龙头大山;看水,看的是控引山泉、合流成溪。听历史,听的是红军长征过龙山、老鸹山剿匪战斗的故事;听传说,听的是郭公买田、陈伯戒赌、刘二创业的教诲。品人物,品的是油画家王大同先生。天与雄区,地因多景,人因才俊,此地山光水色、天然画意,是否能让你眺望抒怀?
风景这边独好
龙头大山,旧称笼纳山,属苗岭山脉,横卧于安龙、兴仁、贞丰三县。《贵州通志》云:“在城北六十里,自普安县境抵达永丰州西南,绵亘数十里,丛林茂箐,中有一溪,源深流长,灌田数千亩。”《兴义府志》有“笼纳山,在城北六十里”“北乡永化里,凡四十六寨”的记载,四十六寨中有两寨分别叫上笼纳、下笼纳,依据寨名,将境内横卧的蜿蜒起伏之山脉称为笼纳山。因何叫龙头大山?《安龙县地名志》说:“因山体像龙的头形一样,故名。”至于“龙头”下的小镇,则按照“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原则,即“龙山镇因龙头大山得名”,是为龙山镇。按照黔西南州博物馆馆长龙虎的解析,“笼纳山因主峰像一条巨龙昂首,民国时期改称为龙头大山,1932年,按贵州第三行政督察区公署令,安龙县于此设龙山镇,便因之得名。”
实际上,“抛”却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沿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算起:1950年8月建龙山乡,隶龙山区;1951年10月隶第四区;1953年4月设北乡,辖一至三村;1955年7月改四区为龙山区,北乡隶之;1958年12月设北乡公社,隶龙山区;1959年1月设北乡管理区,隶龙山公社;1961年10月复设北乡公社,辖10个大队,隶龙山区;1984年7月设北乡乡,辖10个大队改为10个村,隶龙山区;1992年“建镇并乡撤区”设龙山镇,辖30个村,隶安龙县。自此,“龙山镇”一名沿用至今,虽期间行政区划略有调整,但镇名一直未变。
兴仁、贞丰“包揽”了龙头大山的龙身、龙尾部分,安龙却独占龙头,而龙头又尽在龙山镇境,却不知这龙头一带景致如何?且不说众所周知的公龙山、母龙山,这里只拣几处“冷门”地方来“看看”——
龙头大山的半山腰“点状分布”着一个小山寨——高寨,就从这里“出发”,途经“老虎岩”,翻越“大冲”,约摸四五十分钟就到岩脚了。从此条道上山,须过两道山岩,第一道山岩较缓,“铺”着一条人工凿就的“七十二步梯”(目前部分石梯已无踪影,不足七十二步),犹如一个不规则的“Z”,虽不及重庆深山里的“爱情天梯”那般浪漫,但却也不失神秘,既是人梯又是牛梯,不过水牛身躯庞大不能过,只有黄牛凭借“行动灵活,善于登山”的优势,时常“表演”不一样的“飞檐走壁”。
爬完“七十二步梯”,到得岩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小水井,水从石缝汩汩流出,清冽可人,一次性能供三五个人解渴。饮罢山泉水,再优哉游哉行进五六分钟,抵达第二道山岩。此时再无任何“阻碍”,岩口宽阔,比“七十二步梯”更缓,小路处并无岩,曲径通“幽”,茅草萋萋,一望无际的草坡尽收眼底。
龙头大山芳草遍野,到处是放牛、放羊的好去处,其中以一处叫“大营”的地方为最。此处地势开阔,岩口正下方是龙山场坝。在耕牛很“吃香”的过去,每当“秧把搭在田坎上”,放牛的最佳时节到来。人们把牛赶到山上,便七手八脚在岩口砌上石墙,让牛在山上“过夜”,每天轮流派一个人去山上“清点”牛数,“轮”到的人都有幸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景象。在大营,不管放牛与否,都可“凭吊”古墙遗迹,感受看似“松松垮垮”却历经风霜雨雪、云雾雷电仍屹立不倒的古墙“神威”。
若是四五月,“凭吊”古墙未毕,已被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痴迷、陶醉,不由得凑近花丛,一边“动手”一边“动口”,味道酸酸甜甜。若要“补水”,则径直走向小溪或山涧,喝几口清泉,甘甜可口。不忙的话,或坐在岩石板上静听小河的低吟浅唱,或钻进灌木林寻找猕猴桃“芳踪”,或驻足龙潭之上的岩口感受飞流直下、危岩环拱,若仍意犹未尽,还可尽情探访层峦叠嶂、古木萧森、水库遗迹、山涧溪流、刺竹林、牛旮石……实在“不行”,就请移步到公龙山、母龙山、搭斗山!
追寻历史足迹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87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直属部队及一师过安龙时途经龙山,书写了安龙县红色历史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5年4月16日,红军抢渡北盘江,进入贞丰县境后,红一军团沿白层、鲁贡、册亨县坡妹分三路向安龙县境进发。4月19日晨,红一军团直属部队及一师经坡妹进入安龙县王院,行至笃山,部队休息后,再经花障、顶平到北乡(今龙山),司令部驻现北乡村纳花二组罗姓家族老宅,其余部队沿纳院、坡利,到马路河宿营。红一军团司令部驻扎北乡仅一天,却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红军到产妇向曾氏家做饭,给她3个铜钱,向曾氏烧开水给伤病员清洗伤口,红军临走时给了她一些粮食和18块滇洋,把院子打扫干净,将水缸挑满水,向曾氏感动不已;农民杨东先、吴文贞、王永富等人收留了因伤病不能跟随部队转移的谢连长、副排长吴指挥、卫生员王同志等5名红军战士,除一名周姓红军战士伤好后化名龙恒富生存下来以外,其余4人在农民的极力掩护下进行救治,但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为让红军伤员早点康复,农民吴文贞将家中仅有的两只下蛋母鸡炖了……红军驻扎北乡的一天里,召开群众会、打富济贫,打开地主恶霸蒋德安、蒋兴之的粮仓,并收缴其银钱、布匹、衣物、食盐、肥猪、红糖等救济贫苦百姓。一天后,红军离开龙山“一路向北”,继续朝陕北延安方向前进。
来龙山追寻红军什么?宣传标语、军民鱼水情、红色遗址等必不可少。先看一看龙山镇滴水岩(笃山镇至龙山镇公路9km+200m处的崖壁)上2.72米高的“统一抗战力量,加紧后方生产工作!打富救贫”红军标语;再到位于北乡村纳花二组罗氏家族老宅的红军司令部旧址、安龙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听一听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直属部队及一师驻扎北乡期间救济贫苦百姓的感人故事;最后走一走从纳花通往北乡小学的“红军桥”,从红色资源中汲取奋进力量。
看着、听着、走着,如果有人告诉你,巍峨高耸、令人神往的龙头大山曾经是土匪的巢穴,你信吗?龙山的百姓一定相信,尤其是解放以前居住在山脚下的百姓。据说,每当土匪下山开展“工作”,山下百姓得好吃好喝招待,不然他们便“赖”着不走,“就地”开展“工作”,百姓深受其害。为此,山脚下不少人家被“逼”走。不过,随着全国解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现状”即将改变,“留给”土匪们的时间不多了。
1949年12月,安龙县和平解放。国民党“滇桂黔反共救国独立师”残部以师长贺嵩高为首,常在龙山、马路河、屯脚一带破坏骚扰,断电杆、劫车辆,袭击并杀害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员及无辜群众数十人。由于该匪盘踞在龙头大山,地形熟悉,多次逃脱兴仁军分区和安龙县大队的进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龙山、鲁沟、屯脚出兵,于1950年11月20日合围龟缩在龙头大山贺嵩高部。147团2营5连将其包围后,步步紧缩,连续夺得3个山头,将匪逼在老鸹山上,战斗激烈。此次战斗当场击毙土匪60余人,“师长”贺嵩高及残匪40余人被俘。
如果光听“老鸹山剿匪战斗说明”还差点儿什么的话,请“移驾”龙山镇坡利村顶囊组,那里有“图”有“真相”——2010年,安龙县人民政府在剿匪战斗原址,即龙山至兴仁公路旁树立纪念碑,纪念碑采用当地的鹅卵石制作,主碑书“老鸹山剿匪战斗遗址”字样,另一碑简介剿匪战斗概况。
聆听教诲“三部曲”
安龙县龙山镇有很多传说,比如“朱道台斩龙”、“老鸹山田坝由来”、“扛牛过河”等等,不过,这些故事太过“玄幻”,这里来听听三个“现实”点的故事——
郭公买田。民国年间,一字不识的郭公携一家老小搬到龙头大山脚下一个叫坡桥的地方。郭公不识文化,但通过不懈努力,倒也小有积蓄,于是想着买几亩田过个安稳日子。郭公与卖家谈好价钱,双方经“平等协商”签订了一份田契。到了耕种时节,郭公兴高采烈下田。不料,卖家竟不让郭公引水浇田,却又拒绝说明原委。郭公张大了嘴。郭公只好在大路边摆放一瓶酒、一碗肉,将田契摊开,声明:谁读出田契里的内容,酒肉就归谁。“告示”一出,引来不少人围观,他们中有一人识字。郭公听清楚了,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句:“卖田不卖沟。”郭公找到卖家,“补买”了水沟。郭公又兴高采烈下田,可是依然没水。郭公像上次一样,继续“悬赏”找人读契,又听清非常“关键”的一句:“卖沟不卖堰头。”郭公因不识字接连被“算计”,感到难以容身,只得再次举家搬迁,并告诫后人:要读书识字。
陈伯戒赌。陈伯家世居于龙头大山半山腰的一个小山寨,日子过得很清苦,好在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陈伯觉得生活还算有滋有味。陈伯原先并不沾赌,如此好习惯维持到50来岁。然而,一次赶场,陈伯在“不怀好意”之人的怂恿下,怀着“试一试”的心态在赌桌上“娱乐”了一把,第一次“出手”便收获满满。从此,陈伯“爱上”赌钱,且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欠下不少赌债。一天,一群人来陈伯家讨赌债,陈伯儿媳妇正在灶房里煮猪食,尚未出锅,众人根本不理睬陈伯儿媳妇“先舀猪食出来”的苦苦哀求,硬是把猪食泼在灶头边,将大铁锅扛走。为改变“现状”,陈伯决定到地主家当长工。年底结算工钱时,陈伯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一次性领取了全年工钱——60块大洋。父子四人大踏步往回走,路过龙山场坝时,见一堆人正在表演“钱戏”(赌博的一种,即以猜铜钱的正反赌输赢)。陈伯“赌瘾”发作,不顾儿子们的再三阻拦,毅然决然“猜”了一回。果真“一局定输赢”!当碗翻开,陈伯瞬间傻眼,刚领到手的60块大洋还没捂热就“长翅膀”飞了。陈伯回到家里,如患大病一般卧床不起,据说三天不吃不喝,差点“病”死。“活”过来以后,陈伯痛定思痛,决心戒赌,同时立下家训:不准赌博。
刘二创业。小鸡蛋是怎样变成大肥猪的?话说解放以前,出身贫寒的刘二靠给地主家放牛过活,常年穿着草鞋或者光着脚板在龙头大山脚下的山野间奔走。一次,刘二在山坡上无意间捡到一根精美的烟杆。有人拿一个鸡蛋来交换,刘二不“识货”,“买卖”很快达成。刘二揣着鸡蛋回到家,没有“取锅烧油”,而是在衣服胸口处缝了一个口袋,将鸡蛋装进去捂住。不久,一只小鸡娃破壳而出。刘二对这只小鸡娃细心照顾、精心培养,小鸡娃没有辜负刘二的期望,快速发育、迅速成长。这是一只母鸡,正合刘二心意。待母鸡下蛋,刘二舍不得吃,攒起来,以作孵化之用。刘二有了第一窝小鸡做“本钱”。等到第二窝小鸡破壳而出并长大成鸡,刘二仍然舍不得卖、舍不得吃,继续“鸡生蛋、蛋生鸡”,逐渐发展成一群鸡。后来,刘二将鸡群“变成”一头母猪。母猪很“给力”,不久生下了十几只小猪娃。刘二喂养半年多,猪娃们一个个“出落”成大肥猪。
小地方走出大人物
“王大同,男,布依族,1937年生,贵州人。擅长油画。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油画学会会员,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与跨世纪接班人导师。曾任四川美院油画教研室主任。”这是“百度百科”对油画家王大同先生的“定义”。
王大同者,安龙县龙山镇巧岭村人也。在龙山镇这个“小地方”,竟诞生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油画大师,不能不说很传奇。根据王大同先生的自述,上中学时,他经常背着上学物资从巧岭老家步行四五十公里到安义学校读书,求学之路何其艰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终至成功。王大同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而是自身努力。
龙山“小地方”走出的大人物——王大同,被誉为“绘画艺术大师”,他的《雨过天晴》(获全国美展二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布依乡场》(获全国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母亲怀抱》(曾创中国海外展售价记录)等油画作品蜚声海外,代表作品被编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卷、《当代中国油画》《中国美术五十年》等典籍。
来龙山,一定要品的人物非王大同先生莫属,并非他及他的名字、作品名扬四海,而是他对家乡安龙所作的贡献。
王大同大学毕业后一直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直至退休,虽终身未在家乡工作,但他始终挂念着家乡,希望能做点儿什么。王大同做到了,有招堤上矗立的布依女杰王囊仙铜像为证。
王大同在《画室独白——沉默语言伴我行程》中坦言:“1998年,家乡的贵州省布依学会领导王思明、王秉黎、王永尧等发起募捐,纪念‘南笼起义’200周年。南笼就是我家乡安龙200年前的县名,起义领袖王囊仙是布依人的骄傲,和她同属一县也是我的荣誉。为她塑像是在全省范围募捐的,同县的布依人,加上高中同班老大哥王永尧的推荐,做雕塑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为此我回乡到王囊仙的村庄。村头立着一跟木头,是囊仙的雕像,也有眉眼,土人年年祭拜,据说可保风调雨顺。但那木像有些让人目不忍睹,原始粗陋不说,为了防腐还有薄膜塑料包住,不伦不类欲笑不能而顿然愧疚痛心。未能对家乡尽一点力是我艺术的失职,也对不起家乡父老。那之后我竭尽所能塑造了心中浮现的女英雄,她应当美丽而有布依人的诚朴,向天挥手唤起民众,手握宝剑统辖万军。”经过努力,终于“这座雕像青铜锻成,高5米,底座拟布依铜鼓造型,赤铜锻造,高2米,矗立在城北陂塘海十里荷海中的一个小岛上,成为著名黔西南风景区招堤中的一道风景。”不仅如此,他还于2007年画成《王囊仙﹣布依族农民起义女英雄》(又名《王囊仙》)油画,通过这张超大型油画以展示历史和人文,用质地精良的亚麻布做底,幅面高2.78米,宽7.8米,由四张立幅组成,可惜“这画的命运不好,画幅过大,描绘的事件鲜为人知,无人感兴趣,由它放着吧。”
2017年9月20日,王大同先生逝世,享年80岁。“这使四川美术学院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中国美术界失去了一位油画家,布依族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艺术家,而我失去了一位亲密兄弟和挚友。”他的好友王永尧先生在《追忆布依族油画家王大同》一文中如是评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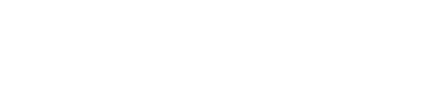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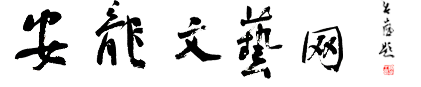



 热门阅读
热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