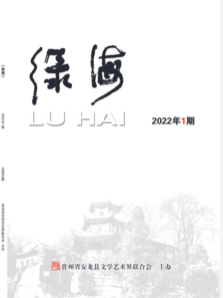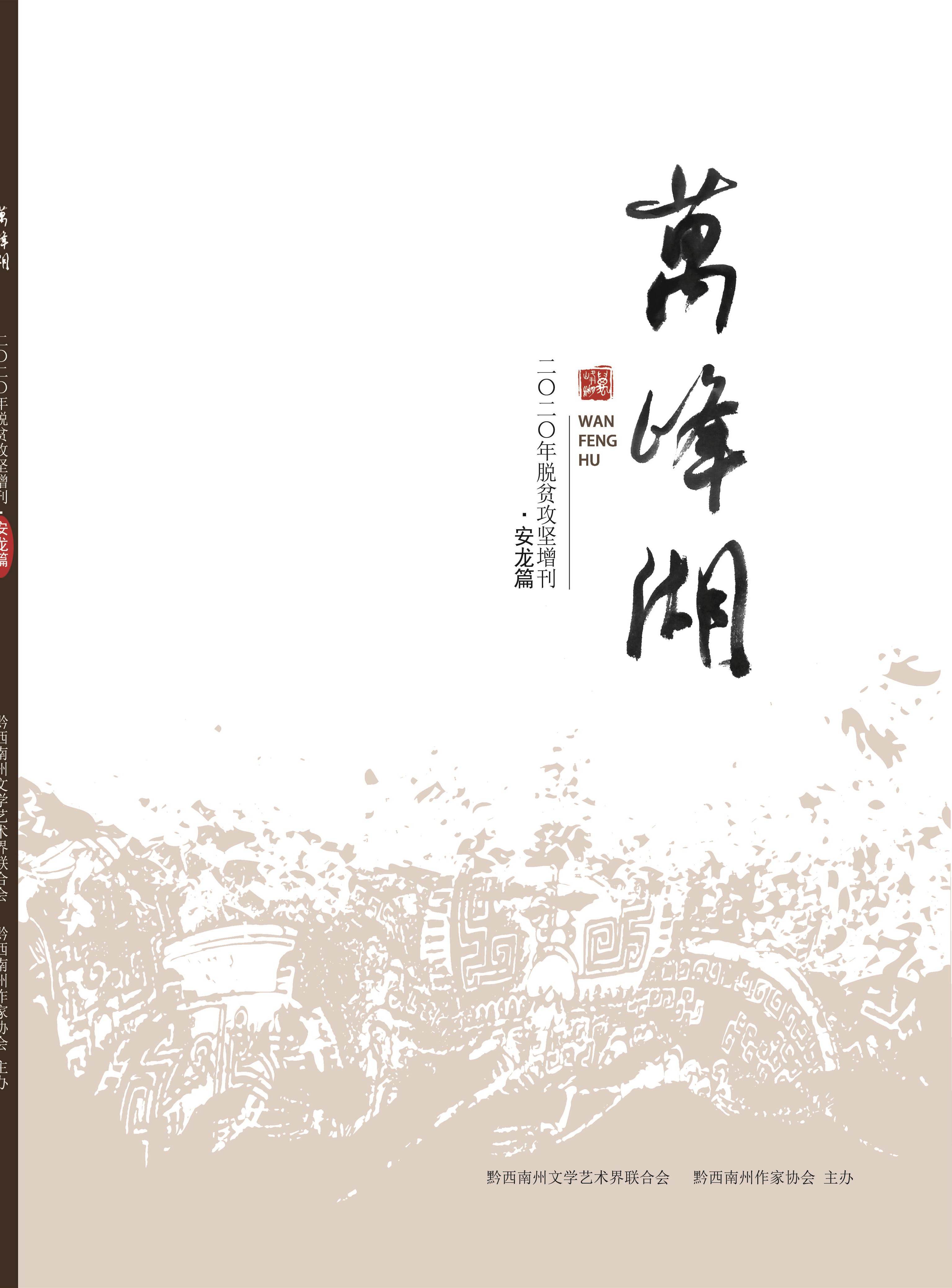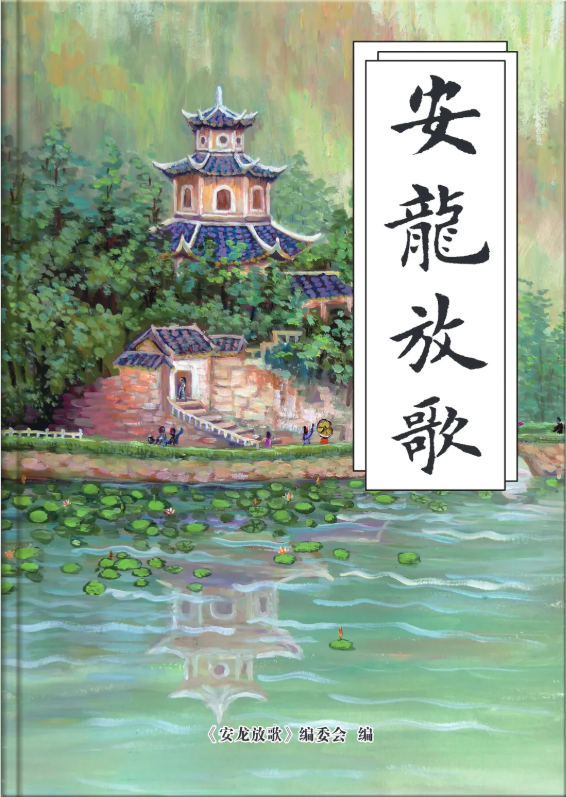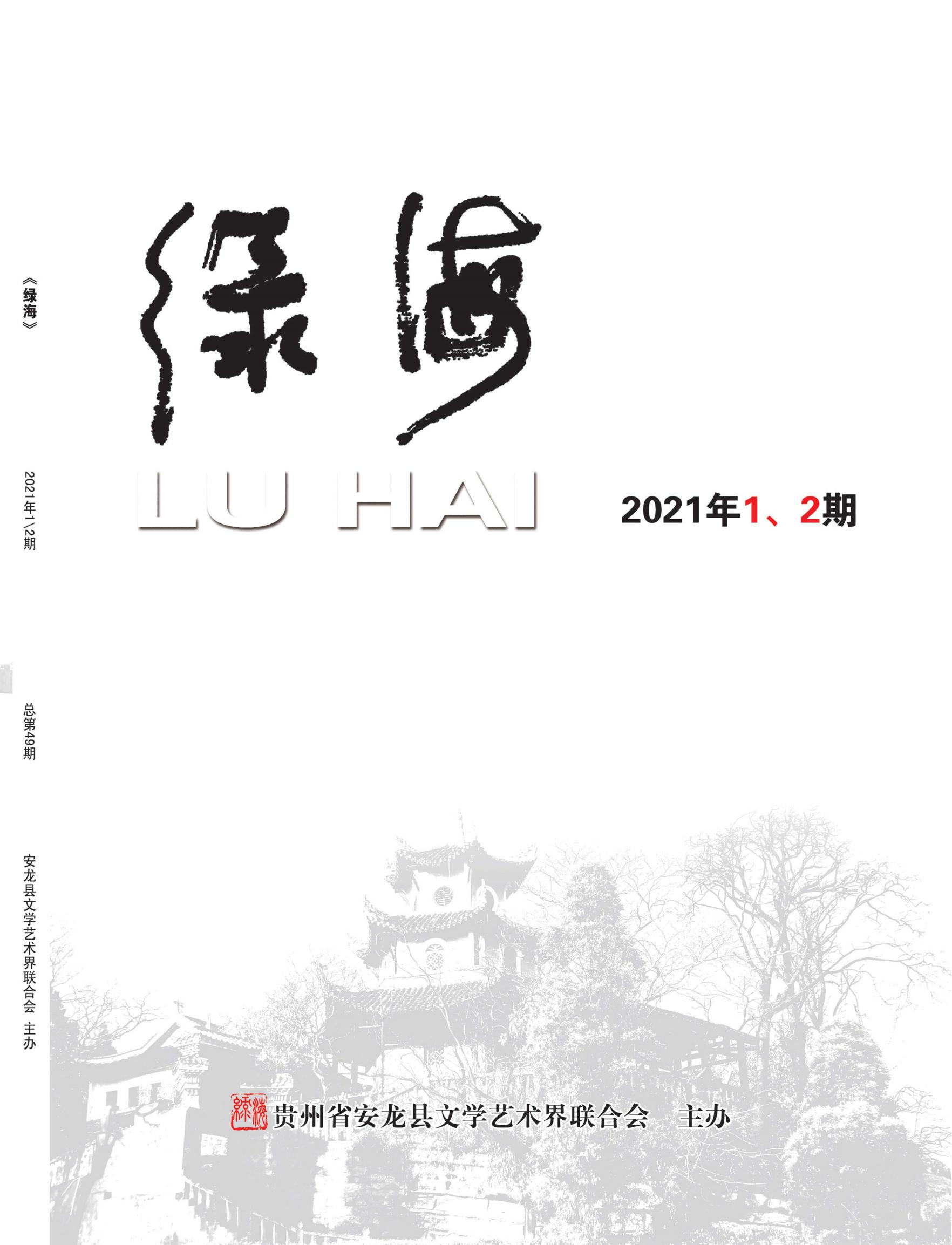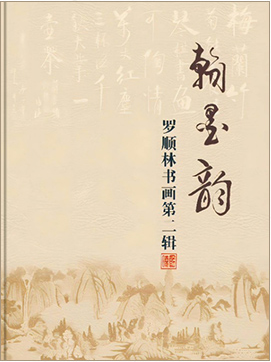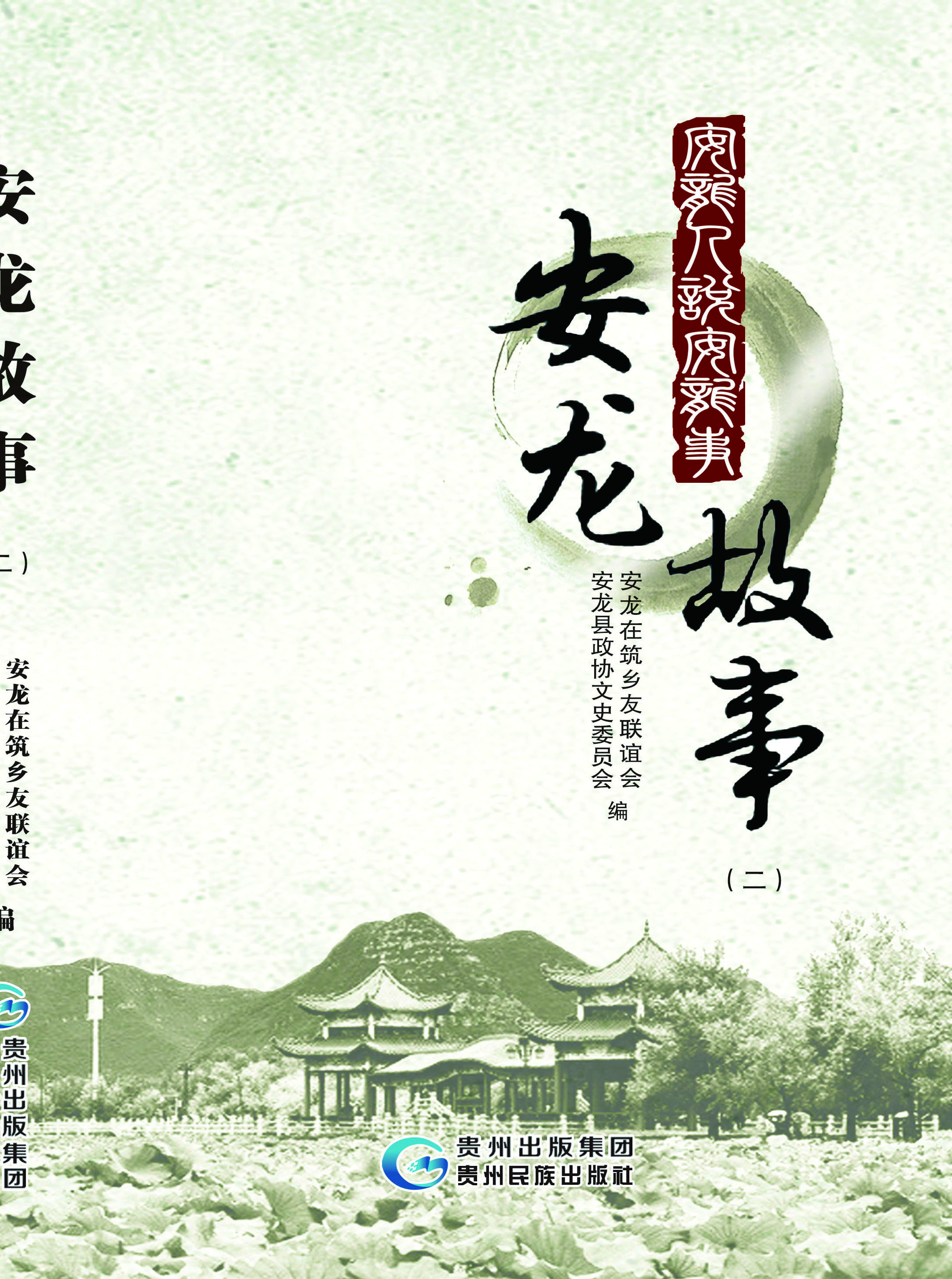一九六六年,我在安龙中学读初三,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老三届”中的一员。
临近毕业,但学校基本上没有出现现代中学生们所面临的高考、中考的“决战”气氛,其压力似乎可忽略不计。要知道,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学就已经有几分了不起。全县二十几万人,读过中学的不过区区数千人,难怪后来中学生会被赐以“知识青年”的桂冠。
到年中,“文革”风暴已初见端倪,学校的政治活动明显增加。这时,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向下传达,其中就有“……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精神。遵循最高指示,县政府、县教育局雷厉风行,抓紧贯彻落实。作为典型的农业县,安龙除了一个小作坊式的机械厂,没什么工业,无学工条件。学农嘛,不少学生来自农村,多少都干过农活,加之学校有农场,各班定期轮换到农场劳动,农忙时还常常组织学生下乡参加“双抢”(即抢种抢收),故学农应该是早已在进行中。学军,由县人民武装部组织军事训练,那确实是便于落实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了。
鉴于当时社会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说实在的,当时的中学生除了多识几个字外,也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说孤陋寡闻也不为过。所以当班主任邹金秀老师宣布即将军训的消息时,仿佛炸了锅,大家兴奋、激动、欢呼雀跃,那毕竟是我们十多岁的中学生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啊。
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为期一周的军训终于开训了,参训人员为全校初一至高三共十五个班级的六百余名学生。开训仪式上,由县武装部王作诗政委作动员报告。在这之前,王政委曾在安中为我们作过时政报告,他那魁梧的身材,黧黑的脸庞,洪亮的北方口音,极富鼓动力的手势,早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除了服还是服。时隔半个多世纪,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分析当年国际形势时说过的那三句话: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当时,几百名直接坐在地上的学生,鸦雀无声,眼睛盯着他,他那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几下就把我们的情绪调动起来,青春的热血在胸中激荡,恨不得马上投入到军训中。
相比现在的中学生军训,我们的军训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着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百衲衣、补疤裤,机织布的汉装,土布的民族服装………脚上绝大部分是布鞋,能穿上胶鞋的寥寥无几,穿草鞋也司空见惯。那背包更是让人忍俊不禁,不必说形状差异,光那色调就格外惹眼,花的、白的、黄的、蓝的,可谓目迷五色。背包带嘛,草索、棕绳、布带……能打上背包就行,真是一支不折不扣的“杂牌军”。
可别小看这群衣冠不整的学员们,到了训练场上,那生龙活虎、朝气蓬物的精气神显露无遗。尽管动作常常不到位,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参与劲头,就让人从心底里赞誉。高中的学兄学姐要为初中的学弟学妹做出表率,目然力求做得最棒,初中的学员们不甘落后,铆足劲全力赶超。这种心态的驱使,让训练场上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热气腾腾的场面层出不穷。教官们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因势利导、推波助澜,使学员们的思想觉悟、竞争意识、集体荣誉感、组织纪律性得以大幅度提高。
一天中午,正在午休的我们,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钟声敲醒,广播通知学饺某处突发火灾,要求紧急集合,参与灭火。火情就是命令,各班学员迅速组队,拿起水桶、脸盆飞速赶到试院议事厅边的小池取水,奔向失火地点,或你来我往,或互相接力。奔跑中有人不慎摔倒,咬牙爬起来继续前行;有人衣服被挂破,不觉可惜,有人鞋跑掉了,顾不上捡来穿上,赤脚疾跑一副紧张而又有些忙乱的画面在闪现。十几分钟后,大火被浇灭,警报解除。衣服挂坏的,鞋跑掉的,被火烟弄了个大花脸的,大家互相看着这狼狈样,忍不住调侃取乐,哈哈大笑,根本没有谁去计较那实际上是一场消防演习。啊,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的纯朴、率真、执看。
黎明时分,被训练弄得有些疲惫的我们睡意正浓,被一阵急促的号音从梦中惊醒。“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伴随着通知声,学员们尽管有几分慌乱,还是迅速地跑到学校的老冬青树下集合。学校领导用十分严肃的语气通报,一架窜犯大陆的美蒋飞机,刚刚在城西方向练家湾山上的松林里,空投了特务,要求军训学员配合武装基干民兵,赶赴敌特空降地点,进行合围,迅速将其抓获。说实话,一听敌情通报,大多数人都相当震惊,当时国际形势严峻,不时有美蒋特务被抓获的消息见诸报端,故此时对通知内容信以为真,不容置疑,气氛不觉紧张起来。出发令一下,大家迈开双脚,迅疾朝城西奔去。一路上除了脚步声几乎听不到其它声音,五公里路程,不到一小时即走完,这时天已蒙蒙亮。接受任务后,各班即成扇形从山脚向山上搜索前进。此时谁都把杂念置之脑后,一门心思想着怎样尽快抓住敌特。搜索到山腰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什么人?站住!只见两条黑影从草丛中跳出往山上逃去,大伙拔腿就追,不一会就将两条黑影团团围住,一些性急的同学扑上去就要用木棍揍“敌特”,吓得他们大叫:不要打、不要打,冒出了安龙口音。待把“敌特”伪装扯下一看,哈哈,两名“敌特”竟然是高三班凌厚权、付子冲学长装扮的。一直沉浸在抓“敌特”氛围中的学员们,此时才反应过米这是一场抓捕“敌特”的演习。
那时虽然已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清汤寡肚的饮食是常态。我们又都处于“吃长饭”的年龄,营养一直跟不上身体发育的需要。加之那时是一日两餐,没有早餐,疲乏嘛年轻人还可勉强扛过去,但参训后运动量的突然增大造成的肚子饿就难挨了,胃里常常是“清口水小包一包地冒”。一开饭,蹲在地上就餐的我们三下五除二,风卷残云般将饭菜扫得干干净净。好在学校农场的几十亩地每年可收些玉米等粮食,多少可拿些来补贴伙食。大米玉米混做的“两掺饭”,基本上能让大伙填饱肚子,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也稳定了“军心”。靠着农场生产的黄豆,偶尔能吃顿豆腐,也算“小快朵颐”。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学校饲养的一头肥猪被拉来杀了,让我们当了一回老饕。一钵回锅肉,完胜今天的无数美味佳肴,那狼吞虎咽的神态,垂涎三尺的滋味,数十年过去了,依然难以忘怀。

野营拉练开始了,目的地是距县城约十五公里的兴隆(狗场)。别看这支队伍着装不咋的,但士气绝对高昂,拉练队伍出安中校门,沿北门坡而下,经北大街顺城街出城。学员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口号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引得小城居民走上街头,夹道相望,投以赞誉的目光。初一头阵,高三压阵,鱼贯前进。校刊《战斗报》的成员负责宣传报道,他们鼓动工作非常到位,几下就把大家的劲鼓起来了。拉练伊始,歌声嘹亮,群情激昂,“你方唱罢我登场”,此起彼伏,真是一路拉练一路歌。三十里路程,不到三小时就被我们用脚步量完,在兴隆粮管所的仓库里“安营扎寨”了。第二天天未亮,即进行了紧急集合等训练,很多细节早已遗忘,但有个别同学把裤子穿反了就跑去集合的情景,着实被笑话了许久,轻易难忘。兴隆区的武装基干民兵,为我们进行了攻击敌人山洞的演练。为增强实战效果,还朝天放枪,一时枪声大作,让从未闻硝烟的我们,切实感受了一番战场气氛,心中既紧张又兴奋。军训临近尾声,高潮终于到来,那就是实弹射击,射击地点设在城东缪家庄附近的麦子湾靶场。教官们熟练地拆卸枪械,细心地介绍枪械型号,示范射击要领,强调注意事项。一个中学生,藉此见识了“双背扣”、“汉阳造”、“三八大盖”、小口径步枪等枪械。当亲手握住枪械时,忐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考虑到初中生年纪尚轻,步枪后座力大,为安全起见,初中部实弾射击改用小口径步枪,每人射击三发子弹。而高中部,则采用七九式步枪进行实弹射击。尽管如此,平生第一次的实弹射击,依然清晰地在年青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五十多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岁月磨灭了不少记忆,淡化了诸多印象,但作为开创安龙县中学生军训先河的一九六六年军训,不仅在安龙中学校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也时不时会在安中老三届学生的脑海泛起阵阵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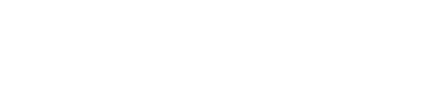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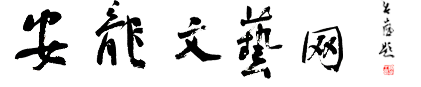



 热门阅读
热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