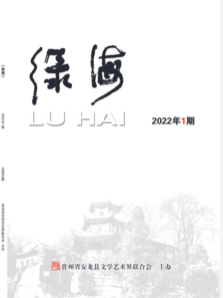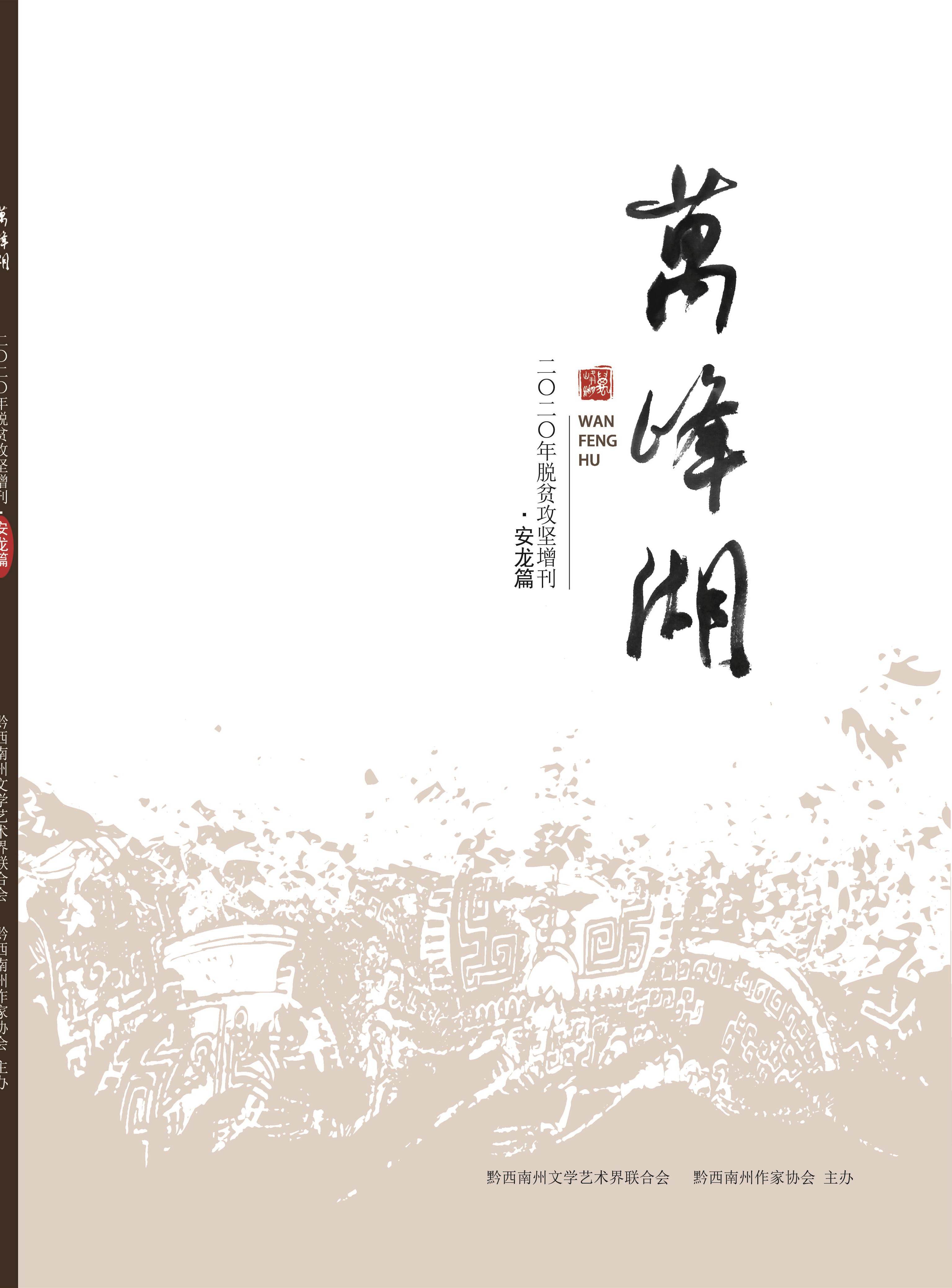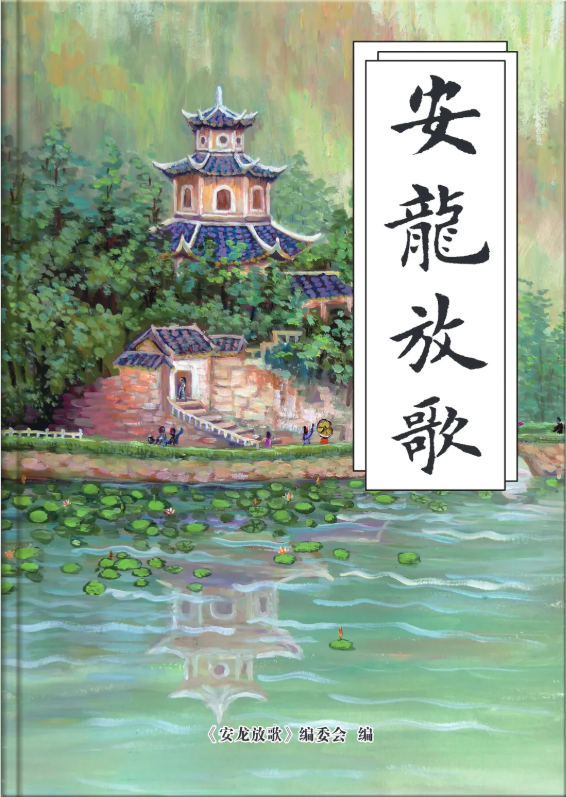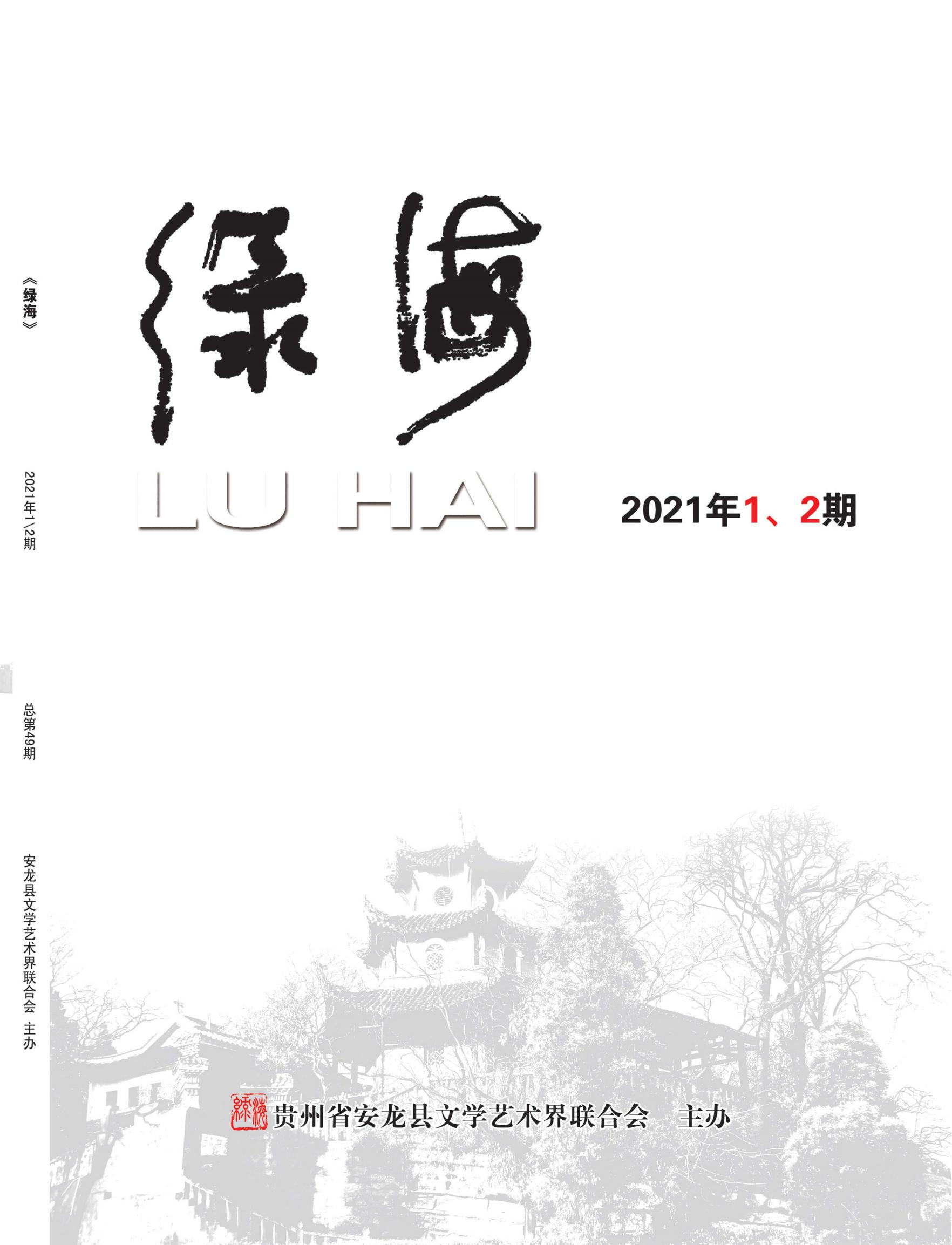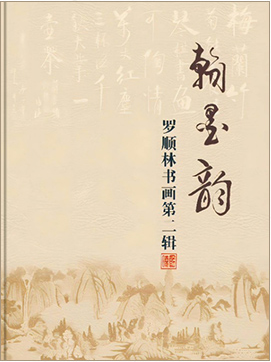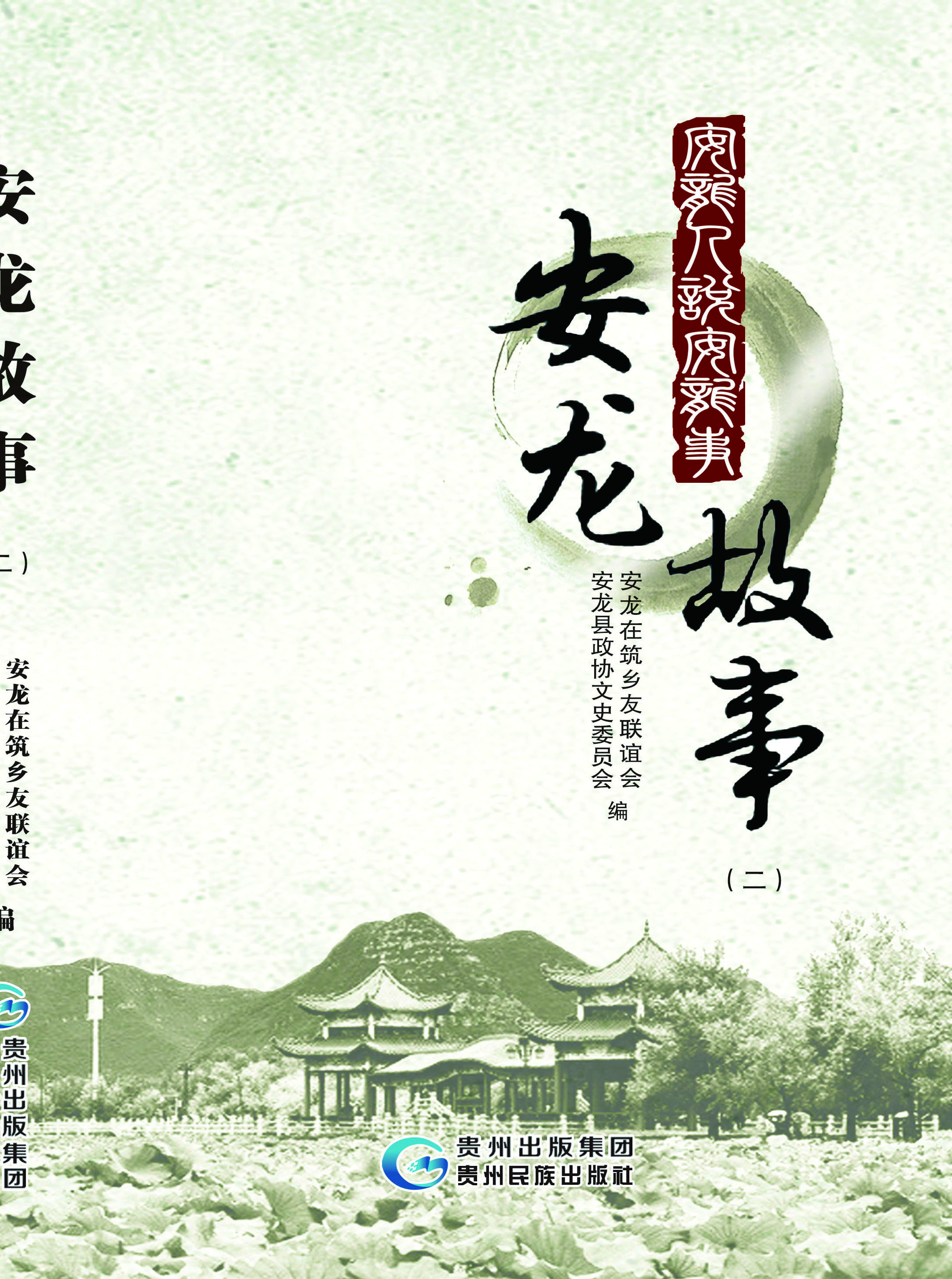不知不觉间,竟然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数十年光景中留在记忆深处的许多东西,也悄然发生了嬗变。曾经的恩恩怨怨,淡然了;那些耿耿于怀的,释然了;过去斤斤计较的,漠然了。反而是那些年少时沉淀在脑海中的依稀往事,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并逐渐显得鲜活起来。它夹带着几分温暖和幸福,让人回味、咀嚼。乡人常说老还小,我想,除了老了会出现类似小孩的举止行为外,这类喜欢回忆儿时故事的情形,大概也包括在内吧。
和无数经历过贫困,饱尝过饥饿的人一样,小时候,一年到头最最企盼的不外乎这么几件事:排头的肯定是盼过年;再者当是盼吃酒了(方言中吃酒指参与红白喜事,以及乔迁“烧锅底”等酒席);排在第三的,应该是盼赶场了。有这样一句童谣:“赶场赶场,又买粑粑又买糖。”纯真的盼望,跃然眼前。逢年过节,吃酒赶场,是我等孩童“饿馋”的绝佳机会,自然能混得个肚儿圆。民以食为天,大人小孩,概莫能外。
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日子逐渐有了起色。快过年时,母亲托赶马车的张叔将乡下的表弟带进城来。有马车坐,第一次进城的表弟带了不少吃的:糯米、晚米、豆米等杂七杂八装了满满一背篼。和表弟相逢当然高兴,更高兴的是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吃的,看着它们眼睛仿佛亮了许多。
当看见母亲将表弟带来的晚米用筛子筛,簸箕簸,专注地挑拣出混杂在米中的细碎石子和谷粒时,我心中窃喜:要打饵块粑了。
也许是对打饵块粑的关注度高,几十年的岁月仍未能将其中的细节磨蚀抹掉,说它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点不为过。选好米,母亲将米倒入大木盆中用水反复搓淘,差不多不见浑水后再放水浸泡。只有经过这样反复搓淘的米打出来的饵块粑才会质地晶莹光润,色泽白净诱人。
待米浸泡一两天,母亲从阁楼上翻出一年难得用上几回的大甑子,将米滤干上甑蒸,这就是所谓的蒸头道。这道工序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将蒸熟的米倒在大簸箕里弄散晾开,让其自然冷透后即可送到打饵块粑的人家进行加工。
那时候,小城周边开这种季节性加工作坊的不下十几家。挣点加工费,赚些小钱。哪家收费合理且打出的粑粑质量好,自然口耳相传,故声誉好的人家必然生意好。人们趋之若鹜,排队等候至深更半夜也心甘情愿。好不容易打回饵块,谁不希望吃起来爽口称心呢?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能玩尽量玩。平常家里有什么事需要帮着做时,常常会扯故躲开,能扯尽量扯,实在扯不脱才极不情愿地翘着小嘴去做。到打饵块时,情形却为之一变。不用招呼,自然凑拢去,装模作样地帮着拿这背那,像跟脚狗一样尾随去加工坊。目的不言而喻一一可趁机让小嘴打打牙祭。
碓,是打饵块的必备工具,碓头重碓窝大,一次加工的量就多且易将米春茸。打饵块粑需要的人手多,开加工坊的人家里要么人强马壮,要么请上几个气饱力壮的汉子,如果有女同胞参与,也都是“不让须眉”级别的,因为春碓绝对是个力气活。
打饵块的第二道工序在加工坊开始,体现技术和经验的招数也在这道工序中展露。米在蒸第二道时需洒些水,称之为分水。水量多少直接影响蒸出的米的干湿度。洒多了发稀不易成型;洒少了显干不易春茸,米粒夹杂影响口感。上甑蒸后的火候拿捏同样讲究,全凭经验临场把握。火候不到或过了肯定影响品质。待蒸好的米从甑子里倒人碓窝时,弥漫的热气夹杂阵阵香气吸进鼻孔,惹得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
碓声响起,热闹的气氛一下子铺开。此时春礁人一反平常春米时的那种懒洋洋的状态,猛踩快放,一脚撵一脚,节奏很快。低头弯腰在碓头搅和米团的师傅更是眼疾手快,既要迅速翻动米团使其受力均匀,又要防止被碓头、碓嘴砸伤,真有几分惊心动魄。
待在碓头搅和的师傅喊出一声“好了”时,碓头高高扬起,一大团冒着热气的粑粑从碓窝里捞出捧到案板上,早在一旁等候的人们手上抹油迅速将米粑等分为约一斤半左右大小的坨坨,然后全力搓揉,趁热、软时将其定型成长而扁圆的枕头状,打饵块即大功告成。此时,等待在一旁观望的孩子关注的却是黏在碓嘴上的或分割后剩下的小团粑粑,被称为“收头粑”,这才是企盼犒赏之所在。这小粑粑,绵柔香糯,嚼着津津有味。几坨下肚,馋虫即被驱赶。当然,我们偶尔也遭掌碓师傅戏弄一下,他常常装作将小粑粑递给你,待你伸手去接时却将其送人自己口中,让你空欢喜一场。待小肚子填饱后,“收头粑”派上了新用场。用还有些绵软的粑粑捏小人或小动物,信手搓捏,似人非人,似马非马,颇有些抽象派作品的味道。当然,这些表面已有些黑黢黢的作品,最后的归宿也是下肚了。
年少时,只知道晚米可以打饵块,其他的浑然不知。待长大下乡当知青后,才对晚米有所了解。它是介于糯米和黏米之间的一个米种,具有糯米的清香,黏性不如糯米;同时又比黏米黏性好,做成粑粑易成型。晚米分为红壳晚和花边晚两大类。红壳晚打成的饵块粑,质感偏硬,筋丝好,耐嚼;花边晚偏软,适口。晚米是一个分布地域较窄的米种,贵州境内主要分布在黔西南,黔西南又以安龙为主产区。安龙的木咱、兴隆、平乐、龙山、龙广等地的坝子均有出产。独特的米种造就了独特的食品,饵块粑绝对是安龙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
安龙地区传统米制食品种类繁多,诸如糍粑、饵块粑、粽粑、泡粑、沙糕、剪粉、米线等等。倘若将这些食品进行比较,口味各有千秋,食人各有所好,不好对比。但如果从保存、吃法方面进行比较,饵块粑绝对是其中之翘楚,其他食品只能望其项背。从保存上看,除糍粑、粽粑能存放稍长时间外,其他食品基本上现做现吃,隔夜甚至隔一个下午,口感都要大打折扣。而饵块却不同,成形的饵块冷却劲皮后,用干净的棉布或纱布包住捂上几天(主要是防止表面开裂),待水分收得差不多,即可打开放人缸、桶等容器中,注人清水浸泡,隔三岔五清洗一下表面黏腻之物,再换上清水,由此放上一两个月其味不变。在无冰箱、冷柜等家用电器的年代,哪种食品能与其比肩?
说起饵块的吃法,那绝对值得叙述一番,烤、煮、炒、煎、炸、焖,样样可行。过去百姓冬季取暖,常提火笼、烤火盆、围火堂,切几片饵块火上一烤,不一会就“两面黄”,外脆内软,看着都诱人。更有吃货嫌这样光着吃不过瘾,做上一碗豆豉辣椒水,用饵块一蘸,吃得嘴里丝丝响,额头冒微汗,真是一个爽;想吃汤水的,烧开红糖甜酒水,饵丝放入打个滚,热腾腾,香喷喷;想吃油的,用猪油、肉丝(片)吊好汤,放人胡椒、酱油等调料,薄饵片下锅烫软舀出,撒上葱花,有条件时放上些豌豆尖(苗),一清二白,看着就开胃。炒着吃,花样也不少:香肠冲菜炒饵丝,或鲜肉韭黄炒饵丝,或鲜肉花菜炒饵丝……食之香糯爽口,忍不住大快朵颐。至于用饵块下火锅,饵条加进焖烧肉食中,则又是别出心裁的吃法。那绵赳赳的饵块吸入其他食材的香味,吃起来满口生津,回味无穷。
时过境迁,当年打饵块时的欢愉、欣喜,在解决了温饱,正在奔小康路上急行的人们身上已难觅影踪。那打饵块的木碓,差不多消失殆尽,几成文物,取而代之的是效率高得多的机械。真空包装将饵块的保质期大大延长,一年四季皆可品尝。晚米供不应求,导致用其他米种替代,香糯的口味较之过去逊色不少,多少让人有几分遗憾。尽管如此,饵块粑作为乡人馈赠外地亲友的特色食品,依然大受欢迎。经过政府、商会、商家、加工户等多年的宣传、推介、展销,“安龙饵块粑”已声名鹊起,成为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品牌。十数家在这个品牌下冠以“某某记”、“某某家”商标的加工户生广的饵块,风光地摆上了超市、商场的柜台,销售地域从县内外拓展至省内外。
追昔抚今,饵块粑这种安龙地区既普通而又极具特色的食品,它的制作、品质、需求、销售的变化,或多或少都烙上了时代变迁的印记。它以独特的风味,花样繁多的吃法,迎合着不同的消费群体的口味,越来越受到更多食客的青睐。可以这么说,凡是享用过它的人,都常会被它的色、香、味所吸引,难以忘怀,更何况一个已食用它数十年的老人呢。你说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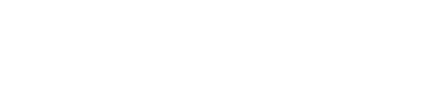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地址: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道办龙顺社区杨柳街4号  电话:0859-5213612
电话: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传真:0859-5213612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工作邮箱:529240925@qq.com 
 关注公众号
关注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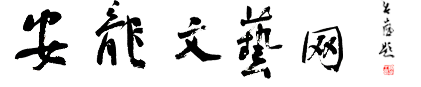



 热门阅读
热门阅读